这是每年春节后,最普遍的情景。
爸爸妈妈要出门打工,骗孩子你也去收拾行李,出来我们一起走。
孩子拿着塑料袋装好小鞋子小衣服,一出门,发现爸爸妈妈已经离开……

每一次看到,都让人揪心不已。
“心都碎了,那一脸的泪水里面有多少辛酸和无奈。”
它会伴随留守儿童的整个童年时光。
网友贝塔说,爸爸在她8岁时得了尿毒症,妈妈带爸爸去北京看病。
她被扔在亲戚家,“天天数着日子等妈妈回来”。
爸妈住在北京亲戚家,当时长途电话贵,没有人让她给妈妈打电话。
她偷偷翻电话本,知道了北京亲戚的电话,趁亲戚不在家,偷偷打了电话。
“那个电话号码,我看了一遍就记住了,现在二十年过去了,我还没有忘记。”
贝塔爸爸妈妈的离开只是短暂的,但对留守儿童而言,“长久的离别”是从小就要承担的必修课。
爸妈为什么离开家?
“土地贫瘠,庄稼收成全靠老天的眼色。风调雨顺,则有收入,反之,一年的辛苦就会付之东流。”
外出打工,才能有钱供孩子读书。
对晓莹而言,情况更为艰难。
爸爸去世时,晓莹才6岁。当时,晓莹的哥哥正在读高一。
家里突遭变故,读高一的哥哥提出退学帮妈妈分担家庭重担。
妈妈一个人供两个正在读书的孩子,实在太困难了。

晓莹和妈妈
她肩上还有晓莹爸爸看病欠下的债务需要偿还。
为了赚钱养家,妈妈只能外出打工。
晓莹妈妈文化程度不高,只能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。重体力活辛苦一个月能挣两千七八百元。
为了能多挣点,妈妈还兼职为工地上的工人做饭。
一人打两份工,起早贪黑。
因病致贫是一部分原因,“妈妈走了”是另一部分家庭面临的困境。
“9年没有见过妈妈了。”
“妈妈离开这个家的那年,湘湘8岁。”
妈妈一走,家里成了只有爸爸的单亲家庭。
爸爸不得不“抛下”年迈的父母和尚幼的孩子去城里打工。
但实际上,出去打工的爸爸妈妈们,在大城市的生活也不容易。
玉玉的爸爸在一家公司做保安,今年整整20年。
公司里的同事像流水的兵,总有人选择离开,也不断有新人进来。
只有玉玉爸爸一直在坚守。
去年,终于付出也算有了回报,玉玉爸爸被提升为公司的客服主管。
金平的爸爸刚去北京也是做保安,工作相对轻松,但工资低。
他在工作之余,学习了木工,后来如愿跳槽去建筑工地当木工。
收入虽高,但他依然不敢懈怠,在北京的郊区租住在每月600元房租的平房里。
金平的妈妈也在北京,是在一家宾馆当服务员,吃住在职工宿舍,每天两点一线。
夫妻两个虽然同在北京,但在2000万人的大都市里,见一次却也并不容易。
爸妈为什么不回来?
金金是甘肃武威的初一学生,爸爸妈妈在北京一家电子工厂承包了食堂,全年几乎无休 。
金金一年最多只能见父母一面。
金金的爸爸是一名退伍军人。在部队里,他学会了一手好厨艺。
退伍回来后,他一直想从事与厨师相关的行业,但在武威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。
一心想干出点事业的爸爸,和金金妈妈一同去了北京。
在战友的介绍下,和别人合伙承包了一家电子厂的食堂。
电子厂在郊区,周围没有学校,加之食堂的大小工作全靠夫妻俩经营,根本无暇顾及孩子。
他们只好把当时年仅10岁的金金留在了老家。
去年春天,金金上六年级,期中考试完要开家长会。
老师说,这是小学的最后一个家长会,必须要爸爸妈妈来。
金金给爸爸打电话,希望爸爸来参加。
爸爸刚说出,爸爸很忙,金金就在电话里哭了,哭得很伤心。
听到孩子的哭声,爸爸心里一阵心酸,一咬牙,把食堂交给了妻子,立即买了火车票。
回到武威,爸爸如约参加了儿子的家长会,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北京。
虽然和爸爸的见面只有短短1天,但金金心里却甜了好久。
每天中午1点多,食堂里闲下来之后,爸爸妈妈都要和金金视频通话。
金金说,那是最幸福的时刻。
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,但现实是,外出打工赚的钱,远比在家乡务农来得多。
懂事的金金说,他能理解自己的爸爸妈妈。
每天能打视频电话,长大到10岁,爸爸妈妈才离家,金金可能是留守儿童里比较幸运的一类。

在《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》中,有一连串惊人的数据:
10%的留守儿童,认为父母已死,
260万的孩子,一年连父母的一个电话都接不到……
很多时候,孩子把见父母最后的期待放在了过年。
安徽男孩小俊,爸妈离异后,一直跟着奶奶生活,妈妈好几年没有回来。
到了腊月二十八,小俊给妈妈打电话说:”妈妈你为什么还不回来?”
妈妈说:“我今年可能回不去了。”
小俊也没哭闹,第二天早上,他用一个塑料袋拧成一根绳子,把自己吊死在自家的卫生间里头。
关注留守儿童问题6年的前媒体人刘新宇说:
“孩子自杀不是因为穷困,甚至不是因为孤单寂寞,而是因为绝望。
他一定是对自己的价值,产生了一个负向的答案:我活着还是死了,没有人会在意,那我在这个世界上,有什么意思?”
让人羡慕的“小候鸟”
小时候,玉玉想爸爸了,经常吵着要去见他。
后来长大些,她渐渐理解妈妈的难处。
爸爸在外做保安,妈妈在家照顾两个孩子一个老人,还要去附近的园区打工。
去一趟北京的花费,是十分奢侈的。懂事的玉玉把心事埋进了心底。
暑假她有更重要的事情做——帮妈妈去地里干活。
烈日下,火辣辣的太阳照在她稚嫩的脸上,满身豆大的汗珠。
“妈妈一个人太辛苦了,要种地,还要打工,我要帮助她,减轻她的负担。”
相比之下,湖南衡山县的兄弟俩可能会让玉玉有些“羡慕”。
20年前,17岁的王斌跟着南下打工的大潮,去到广州打拼,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。
如今王斌和妻子刘敏长期在广州务工。
每到暑期,王嘉鑫和王嘉广俩兄弟都会跟随奶奶,一起前往广州和父母团聚。

5点天不亮就起床
去年暑假,一家人提前几天抢了几次硬座无果后,最后狠心买下软卧。
在王嘉广的心里,从老家到广州是一段越走越长的旅行。
这种记忆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清晰。
“小时候和妈妈一起坐火车很快就到了,现在觉得火车开得好慢。”
王嘉广站在过道里望着窗外,会一直询问奶奶还有多久到广州。
第一次坐软卧的王嘉鑫有点兴奋,睡不着,去过道瞎转悠。
他碰到好几位都是南下和父母团聚的“小候鸟”。

“我叫王嘉鑫,今年10岁,来自湖南!”
“你好,大家都叫我小胖,我来自陕西汉中!”
“我是王宁,来自西安。”
车厢里,几位小朋友的玩耍打闹让车厢热闹起来。
到了广州,爸爸妈妈接上两个孩子和奶奶,一家人团聚了。

有了孩子的陪伴,让爸爸王斌在广州终于有了“家”的感觉。
“要实现这样的愿望,要么我回家,要么接他们来广州,不过目前看来前者更容易实现。”
但无论如何,暑假的两个月,一家人团聚了。
渴望被爱
2014年,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再度引起了人们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:
在贵州的毕节市有4名独居的留守儿童。
父母早已离婚,妈妈平时不在,父亲又长年在外打工,很久没回来。
十几岁的哥哥,带着3个妹妹生活。
孩子们不去上学,而是选择把自己锁在家里。
6月9号晚上,儿童节刚过没多久,4个小孩自己服下农药自杀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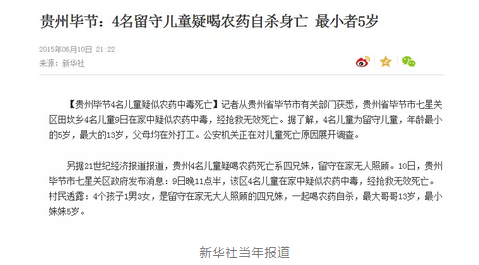
新华社当年报道
四个孩子没有给大人们“添任何麻烦”,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《预防自杀:一项全球要务》指出:
自杀是个复杂现象,极少由单一原因引起。
但显然,这四个孩子选择离开最大的原因是“被留守”,没有人爱。
其实,那些在给大人“添麻烦”的小孩,实际上对美好和被爱还抱有希望。
现实情况是,我们一时很难让务工父母回家,也很难让孩子们在父母务工的城市读书长大。

面对最大基数的留守儿童人群,公益项目一直在寻求妥善的解决之道。腾讯成长守护平台携手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发起的“幸福列车-童画车票”公益项目,计划在今年7月启程,通过回家车票的公益助力,帮助留守儿童去往父母务工所在城市,用一张火车票,让孩子与父母团聚。